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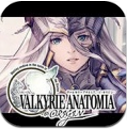

“五一六通知”的发起及其原因探析

1966年5月16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著名的《中国我党中央委员会通知》,即“五一六通知”。这一通知的发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长达十年的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。那么,“五一六通知”究竟是如何发起的?其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?本文将从历史背景、政治环境、思想斗争等多个维度进行探讨。
1960年代初,中国我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了一系列争论。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,党内开始反思苏联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,同时也在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。在这一背景下,中共中央于1964年7月专门成立了领导思想文化工作的机构——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,组长为彭真,成员包括陆定一、康生、周扬、吴冷西等。这一机构的成立,原本是为了加强对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,但在“左”倾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形势下,一系列学术、文艺观点被扣上了修正主义等大帽子,并遭到公开批判。
1965年11月10日,上海《文汇报》发表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,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、历史学家吴晗,称《海瑞罢官》是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,“是一株毒草”。这一事件迅速成为思想文化领域斗争的焦点。在此背景下,文革五人小组于1966年2月制定了《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》,即《二月提纲》。《二月提纲》提出“要坚持实事求是,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,要以理服人,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”。其本意是约束文化领域的大批判,防止其进一步发展为政治斗争。
然而,《二月提纲》的出台并未平息思想文化领域的纷争,反而引发了更为激烈的争论。主席对《二月提纲》提出了尖锐批评,认为其混淆了阶级界限,未能准确揭示出文化领域内的阶级斗争。在此背景下,1966年4月,林彪、江青主持的《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》经主席审阅修改后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。《纪要》宣称建国以来文艺界“被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”,要求“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,彻底搞掉这条黑线”。
随着思想文化领域斗争的升级,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了扩大会议。会议由刘少奇主持,主席、周恩来、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均出席。会议期间,对彭真及《二月提纲》进行了严厉批判,并成立了“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”,成员包括陈伯达、康生、江青、张春桥等,负责起草《中国我党中央委员会通知》。
5月16日,会议通过了由主席主持起草的《中国我党中央委员会通知》,即“五一六通知”。《通知》宣布撤销《二月提纲》和“文化革命五人小组”及其办事机构,提出重新设立“文化革命小组”,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。这一决定是为了开展“文化大革命”而采取的组织措施。《通知》还罗列了《二月提纲》的所谓十大罪状,逐条批判,并提出了一套“左”的理论、路线、方针、政策。
在结语部分,《通知》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《二月提纲》,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,号召向党、政、军、文各界的“资产阶级代表人物”猛烈开火。这些从“左”的观点出发的要求和估计,严重脱离了实际,为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发动奠定了理论基础。
“五一六通知”的发起,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首先,从国际环境来看,中苏关系的恶化使得中国我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更加警惕所谓的“修正主义”倾向,试图通过“文化大革命”来清除党内的“资产阶级代表人物”,巩固无产阶级专政。
其次,从国内政治环境来看,“左”倾思想在党内逐渐占据主导地位。在主席看来,党内存在着一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“黑线”,必须通过“文化大革命”来彻底揭露和批判这条“黑线”。同时,主席也试图通过这一运动来加强自己的领导地位,巩固个人崇拜。
此外,从思想文化领域来看,《二月提纲》的出台未能平息思想文化领域的纷争,反而引发了更为激烈的争论。主席对《二月提纲》的批评以及随后的一系列事件,使得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发动成为了必然趋势。而“五一六通知”的发布,则是这一趋势的具体体现。
“五一六通知”的发布,标志着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正式发动。此后,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批判斗争。在这场运动中,无数无辜者受到迫害和摧残,党的组织和国家机构遭到严重破坏。同时,“文化大革命”也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停滞和倒退,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。
尽管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最终目的是清除党内的“资产阶级代表人物”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,但实践证明这一运动严重偏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。它给中国带来的破坏和灾难是深远的,也是无法弥补的。
综上所述,“五一六通知”的发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它既反映了当时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和国内政治环境的动荡性,也揭示了“左”倾思想对中国我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危害。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,我们应该铭记这段历史,从中汲取教训,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,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。